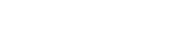王羲之与《用笔赋》原文及释文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小名吾菟田。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渡后迁居南京乌衣巷,最终归隐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王姓本显赫士族,永嘉之乱,西晋灭亡,羲之伯父王导、王敦“建江左之策",成为东晋王朝的开国重臣,王氏家族更迅速上升为东晋士族之首。羲之生于动乱,成年后历任:小官,屡迁不就,官至会稽内史,授右军将军,故后人称其为“王右军”。他的叔伯王敦、王导、王廛,堂兄弟王恬、王洽、王劭、王荟都是书法名手,王羲之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里。他七岁即开始学书,后从叔父王廛,受益匪浅,又从表姑母卫夫人得钟(繇)派嫡传。可以说,书艺兴盛的时代为王羲之的成才提供了宏观背景,而家学渊源则为他登上书艺堂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羲之终以书法闻名天下,真、行草、隶、飞白,“备精诸体”,而行草尤绝,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汉魏的新的书体、书风,在书法艺术领域内最为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又不流于狂放,很好地达到了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美学标准,后人推为“书圣”,古今一人耳。羲之又有风流潇洒超凡脱俗的翩翩风度,在人物藻鉴盛行的晋代,他于少年时即被时论瞩目,形容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美誉为“王氏三少”之首。从政后又被征西将军庾亮赞为“清贵有鉴裁”,其鲠介坦诚、刚直不阿的“骨气”更被当成了评鉴别人的标准。后来唐太宗好其书法,谓之“尽善尽美”,实则亦可用来评其为人。正可谓“人如其书,书如其人”,人品、书风相宜俱佳。羲之又工诗文,其《兰亭集序》最为后人称道,然其诗文却多为书名所掩,亦为书名所彰。
东晋书论颇丰,托名王羲之所著者也有多种。如《书论》,见宋朱长文辑《墨池编》;《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始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又见宋陈思《书苑菁华》;《笔势论十二章并序》,见《书苑菁华》;《记白云先生书诀》,见《书苑菁华》;《自论书》,见《法书要录》,《全晋文》题为《与人书。。。。等等,然可靠性皆很成问题。作为“书圣”的王羲之,无疑是对书法发表过一些看法的,但流传后世、可以肯定的只有见于《晋书》本传及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的一些片段,至于他是否曾著有过系统的书学论著,则难以确考。唐修《晋书》,太宗李世民挂名主编,并亲作《王羲之传论》,其中就未曾言及羲之有任何书学论著,齐、梁至唐代,书评、书史之作甚多,如梁萧子云《答敕论书》、庾肩吾《书品》,唐李嗣真《书品后》、张怀瓘《书断》、窦泉《述书赋》及窦蒙的《述书赋》注,等等,亦皆未提到羲之有书学著作。即便首次引用羲之书法言论的唐人虞世南《笔髓论》也是如此,而唐人孙过庭虽为明确说到羲之书法论著的第一人,但他在其《书谱》中对提到的传为羲之所作的《与子敬笔势论》却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直至唐天宝年间,书法家蔡希综《法书论》方肯定羲之作有《笔阵图》及《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卢携《临池诀》则又提到羲之有《笔势论》。鉴于此,我们对托名王羲之的一系列书法论著的态度应该是:一、在目前无法定论的情况下,则不必再过多地纠缠于作者的问题上,暂且存疑无妨。二、联系当时艺术空前繁荣和高度发展的事实,这些论著以书法美学理论成果的面目出现,从逻辑上讲,是可能的,只不过在内容方面,或许由于流传的原因而有可能加入了些后世的思想成分而已。
《用笔赋》即是托名王羲之的众多作品之一,见载于宋代朱长文所辑《墨池编》。虞世南《笔髓论》中“释草”一节曾有引用,则可知在唐初即已见有此赋。赋云:
王羲之的《用笔赋》原文:
秦、汉、魏至今,隶书其惟钟繇,草有黄绮、张芝,至于用笔神妙,不可得而详悉也。夫赋以布诸怀抱,拟形于翰墨也。辞云:
何异人之挺发,精博善而含章。驰凤门而兽据,浮碧水而龙骧。滴秋露而垂玉,摇春条而不长。飘飘远逝,浴天池而颉颃;翱翔弄翮,凌轻霄而接行。详其真体正作,高强劲实。方圆穷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骨拒筋,含文包质。没没汨汨,若蒙汜之落银钩;耀耀希希,状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飘?骋巧,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季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乔脱屣,焱飞凫而上征。或改变驻笔,破真成草;养德俨如,威而不猛。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争;发指冠而些皆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地。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厥,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非越。信能经天纬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蹉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于今鲜俦。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
王羲之的《用笔赋》释文:
自秦、汉、魏至今,楷书只钟繇一人,草书则有黄绮、张芝,至于用笔的神妙,罕有能讲得清楚的。这里以赋来表达心中意思,将书法的形态用语言文字来说明。辞云:
书法与人的挺秀英发有何不同?那是完美的博大的包含美质的艺术。书法的形态,或如驰走帝门而安定的瑞兽;或如浮游碧水而腾跃的游龙。或如秋露下滴垂挂,光润透明如白玉;或如春风摇动枝条,生机盎然但不见滋长。有时,好像鸟儿飘飘远逝,沐浴云海时上时下;有时,展翅高飞,超越云层连成一线。若详察真书正书,则有高强劲实之美。那吉金刻石上的文字,方圆的变化使金石变得无比美丽,纤粗的摆布使器物显得极为茂密。那线条既有骨气又能遒润,内含古质但外露英华。有时像流水没没汩汩,有时又像日落濛汜,只剩日轮如银钩;有时像黎明天亮,样子像旭日挂在扶桑之下。或许是施展高超的技术,状若飞翔,自然而然,应是包容汇聚了天上神仙。有时像季氏韬光,像隐龙一般沉著内敛,却抒发了怡悦的心情;有时像神仙王乔,脱下鞋子,一瞬之间变作双凫飞空上升。
此外,如果改变真书的驻笔,就能打破真书的清规,变成草书;总之,书法艺术使人学会养德,变得端庄,但又威而不猛。草书的游丝时或中断,但笔意相连,如同龙凤成群而不争;当进入书写状态时,头发似乎指向了冠帽,眼珠子也特别突出,好像手握纯钩,欲上战场忠心耿耿。忽然挥笔瓜割,黑白分裂,但黑白相间的同时又互相交结,成了聚族而居;或如长空的阵云,或如溪谷的卧松。有时又像滔滔江水向东流注,忽然被蜿蜒的群山打了活结,暂时拥塞成渊。对笔法的掌握,既要施展一箭射中雀目的技巧,又要使出力拔长蛇的全力。那弥漫着某种意绪的书写,草草眇眇,简率飘动,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倒,越过嵩山、华山不惧高,越过悬崖履平地。
由于书中法象与自然万象契合,这就要求真正的书者要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辅助王道的修为。如果专心研习、深切玩赏,至少也可以积累如山丘一般的功德。多么秀逸,多么悠久,多么美好,那是英明信诚的哲人,但时至今日,却少有同道。可是,书法的存在将与天地一样永久,与日月一样闪耀;书法的生命,如偃盖于高峰之巅的郁郁葱葱的松木,又如万岁千秋,直到永远。
序文旨在说明创作该赋的原因:长期以来,隶、草等书体各有所宗,代有所传,而具体关于书法如何用笔的神妙之处,则不可得而知之,作者因作此赋加以阐述。接下来则是总写文字产生的不同凡响和书法之美的神奇无比。然后分别以一系列的颇为形象的比喻和描写对真书(楷书)及草书的笔法、笔势、风姿、神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真体正作",则既遒劲如金石,又纤密若凝脂,朴实而不缺丰韵,刚劲而蕴涵柔美;“破真成草”,则或断或续或连或绝,纵横恣肆、秀逸奇拔,自由奔放千回百转,虽乱如飞花,杂若舞雪,而自有章法,浑然天成。在描绘由不同笔法所形成的形式特征时,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动词运用达到了非常形象的表达效果,如“藏"、“抱"“含”、“包”、“断”、“续、“群”、“诤”、“瓜割”、“交结”、“注”、“塞”、“射”、“拔”、“连”、“绝”、“飞”、“舞”、“行”、“止”、“卧”、“蹙”、“透”、“瑜”等等。赋的最后是对书法的赞美。
总观全赋,其序文字较粗拙,全赋与现存羲之其他著作风格亦颇为相异,既不似其存量甚多的杂帖书信那样“精炼”、“通达”,也不像其文学作品如《兰亭集序》那样“调清词雅”。然毕竟赋与其他文体有所分别,又无法见到羲之另外的赋作,难以作出准确比较,只能存疑。而赋中内容又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既言“羽客”,又说“神仙”,还提到道家仙人李八百如神龙隐现、王子乔驾屣而飞的故事,似乎颇能与魏晋时代玄、道盛行的社会背景相应。其二,赋后赞美书法能“经天纬地”,仔细钻研则“功盖山丘”,其杰出者则名垂千古、无人能比、与宇宙共存、与日月同晖,等等。一方面,于王羲之而言,文辞上既不合乎风流雅致、骨气高爽、清峻超逸的“书圣”的口吻,而“耽之玩之,功绩山丘的说法与王羲之对书法的态度也有相左之处。他曾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也。”自述于书法并不像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张芝那样“耽之若是”,否则未必不能超过之。从王羲之的思想和生平看,他颇为关注的倒是实际的社会问题,书法只是作为一种“余事”来对待的,自然就不会如张芝那样的“耽之若是”了。另外,从他的言辞中似乎还隐约透出对张芝如此耽于书法颇为不以为然之意。再有,羲之在谈到“飞白书”时也曾说过“致此四纸飞白,以为何似,能学不?”“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或作,复与卿。”皆旨在说明“飞白书”“至难”又费精力,不如不学为妙。这些都是当时很注意“养生”的世族名士们多把书法当成一种怡情养性的活动,而不主张特别为之苦心劳力的风气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于书法艺术本身来说,也不符合其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为书法虽盛于两晋,在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却并不如此前的两汉和此后的唐代那样显得极其重要(汉代虽有抵制汉灵帝开“鸿都门学"以及赵壹《非草书》等反调出现,但在为统治服务的前提下,书法毕竟颇受重视。),书家多以此来添其名士风流、展现自身人格,属于自觉地追求书法艺术之美,似乎并不以此来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赋中的誉美之辞倒更象是后来唐代书法与政治、教化和个人前途紧密相关的社会普遍意识的反映。
然而,关于“用笔”又确乎是魏晋南北朝美学家和书法家们对书法艺术形式进行考察时,所首先要集中关注和分析的主题之一。索靖说:“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袁昂说:“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庾肩吾又说:“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皆是在以一种错落有致、类似音韵的节奏之美来探讨“用笔”的变化所产生的形式之美。王僧虔则说:“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工之尽矣,可擅时名。”更是把以粗、细为代表的笔法变化看作书艺高低的关键。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章》及《草书状》中还针对“用笔”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成对的概念:“肥瘦”、“粗细”、“疾迟”、“缓急”、“驻引”、“抽点”等等。托名于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并序》及《书论》不但强调了笔法的变化,还分析了“侧笔”、“押笔”、“结笔”等十余种具体的不同笔法及它们所产生的不同的形式效果。而《用笔赋》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对不同笔法的形式特征进行详尽的描绘。仅从这点来看,该赋又仿佛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众多的有关“用笔”的探讨的一种反映。
综上所述,《用笔赋》确实不能轻易被断定为王羲之之作,只能把它看作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书法理论的某些成果的作品来加以对待。而从赋中对书法技巧、笔势、笔法的描述和对书法艺术之美的表现来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该赋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在书法艺术上造诣非浅而又颇具文学功力的人。至于为何会托于王羲之名下,自然是与唐宋时期书坛极度“崇王”的现象密不可分的。
关注微信号:雅墨客书法讯息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