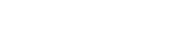黄庭坚在知吉州太和县任上
元丰三年春庭坚入京,到吏部改官,除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秋天自汴京南归,“又持三十口,去作江南梦”(《晓放汴州》,《外集注》卷八)。途中他特地前往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拜会了以孝行著称的徐积(仲车),由扬州溯江西行,过芜湖会李之仪(端叔)。在舒州与舅父李公择聚首时公择为准南西路提点刑狱,逗留期间,他登潜山。山上有山谷寺,为南朝粲代宝志禅师所首建;寺东北隅有禅宗三祖僧璨大师塔,故此寺又称三祖寺。其地又有祠祀道教中的“九天司命真君”,故该山又名司命山。这里可以说是佛道两家的圣地,因而激起了他热切的向慕之意。他在石刻题名中提到“行憩宝公井,瞻礼粲师塔”,还作了三首诗题咏此行,表达了对佛道境界的心向神往。从此他就自号“山谷道人”,这个称号伴随了他大半生,也成了同时代及后世人对他的主要称谓。
黄庭坚在元丰四年到达吉州太和县任。太和在吉州治所庐陵的南面,赣水流经其地从县尉、学官到一县之长,从地位上来说是一种升迁,手中也掌握了处理政务的实权,但他并不因此感到些许的得意,他的内心深处仍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摆脱羁绊,归隐乡里。他刚到任所就写了《到官归志浩然二绝句》,诗中写道:“满船明月从此去,本是江湖寂寞人”,“敛手还他能者作,从来刀笔不如人”(《外集注》卷九)。一个新上任的地方官以诗明志,却发出了归去之叹,声称天下自有治国能人,自己拙于吏事、不善刀笔,正可袖手旁观,显然表现了与当政者的格格不入。由此可见,他的归隐之志是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诗中愤世之情的抒发往往与归隐之志的表述交织在一起。在太和时期的诗作中这一主题依旧回响不辍:“蚤为学问文章误,晚作东西南北人。安得田园可温饱,长抛箐绂裹头巾”(《同韵和元明兄知命弟九日相忆》,《外臬注》卷九)“督邮小吏皆趋版,阳春白雪分吞声”,“莫要朱金缠缚我,陆沉世上贵无名”(《次韵答杨子闻见赠》,《外集注》卷九);“寂寥吾道付万世,忍向时人觅赏音"(《洪范以不合俗人题厅壁二绝句,次韵和之),《外集注》卷九)。
他与现实政治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新法的不满。庭坚在太和任上的元丰年间,适逢朝廷加紧推行食盐专卖政策,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痛苦。他亲眼目睹了民间的苦难,将它们写入诗中,对这一盐法进行 了猛烈抨击,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深刻不满。
为了理解庭坚这一时期的 思想,有必要将北宋食盐专卖的有关问题作一概述。 宋代官盐的榷卖实际已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制度,政府在某些地区强制城乡人民定额认购食盐,甚至不买官盐也得纳钱。政府对官盐实行计口配售,有赊售与现钱交易两类,官方持有卖盐的簿籍,民户则有买盐的“历头”,作为计划供应的依据。官盐由于质次价高,难与私盐匹敌,但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专卖,百姓不得不买官盐,甚至由吏卒配送官盐,届时持簿逐户收钱,凡买足规定盐额的民户可在卖盐簿籍上予以注销。官盐买卖可以各种货币支付,也可折以实物。由于销售官盐关系到盐吏的考绩、前程,因而他们千方百计地向百姓敛索,包括克扣斤两,少支多取,虚计分量,抬高价格,甚至在盐中掺杂泥沙,将折偿物价贬低等等。
在官盐榷卖中江西一向销售的是淮盐,元丰三年蹇周辅擢为三司副使,提出了改革江西盐法的设想:将广南之盐运销于江西南部,将配卖制度推广于江西全境。这一设想获得神宗的首肯后终于成为法令而被推行。这样,虔州与南安军销售广盐,原销于这两地的淮盐则分到其他州军去出售,于是洪、吉等八州军在原有的盐额上又加卖了七百三十六万余斤淮盐,江西一路就新增了一笔“增卖盐钱”,这笔收入不准地方动用,直接由朝廷掌管。向百姓配售“添额”的淮盐是江西新盐法的要害所在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一个新的途径。这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也给地方官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他们既要完成本州卖盐的旧额,又需完成出售加额淮盐的任务,稍有稽迟,即当受罚。
江西新盐法的这些弊端在庭坚的诗作中都有如实的反映。作于元丰五年的《二月二日晓梦会于庐陵西斋作寄陈适用》这样写道:
饱食愧公家,曾无助毫末。劝盐惟新令,王欲茕独活。此邦淡食伧,俭陋深刺骨。公园积丘山,贾竖但圭撮。县官恩乳哺,下吏用鞭挞。政恐利一源,未塞兔三窟。寄声贤令尹,何道补黥刖。从来无研桑,顾影愧簪笏。何颜课殿上?解绶行采葛。(《外集注》卷十)
作为地方官,他有责任向百姓推销官盐,但百姓一贫如洗,俭朴简陋之极,无钱买盐,只能淡食。尽管公家仓库中的盐堆积如山,但卖盐时却要斤斤计较;如果老百姓不愿买官盐,就要遭到鞭打。官府实行榷盐虽能得利,却未能阻止百姓别思对策。目睹这种聚敛刻剥的情景,自己还要参与其事,良心上实在受到很大的谴责,他曾想过如何能补救受残害的人民,但也无可奈何,唯一的解 脱也许只有弃官归隐一途。
这种心情更详尽地表现在他的一组下乡赋盐的纪行诗中。元丰五年三四月间,为配售官盐他曾深入到山区穷乡,目睹了人民生活的种种悲惨景象,写下了十二首纪行诗。最早的一首 题为《三月乙巳来赋盐万岁乡,且搜猕匿赋之....》可见此行的目的除了售盐之外还要搜寻逃避买官盐的人家。《上大蒙笼》一诗写得尤为生动:
黄雾冥冥小石门,苔衣草路无人迹。苦竹参天大石门,虎远兔蹊聊倚息。阴风搜林山鬼啸,千丈寒藤绕崩石。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向来陆梁熳官府,试呼使前问其故。衣冠汉仪民父子,吏曹扰之至如此。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驱使。(《外集注》卷十)
诗的结尾四句可谓沉痛之至。原先是有米无盐,只能淡食,如今是连米也没有了,官府还要强行抑配食盐。“但愿”云云正是一针见血地揭出了官府的抑配目的乃在于聚敛,为统治者着想,让百姓走投无路,无异杀鸡取卵,不如给他们留条活路,也好有子孙繁衍,以供驱使。由此可以想见统治者盘剥人民之惨烈。表面上是为民请命,骨子里是深刻的控诉。在《劳坑入前城》中也写到了同样的惨况:“山农惊长吏,出拜家骚骚。借问淡食民,祖孙甘铺糟?赖官得盐吃,正苦无钱刀。”(《外集注》卷十)山民淡食,莫不是祖祖辈辈甘心吃酒糟?这一问可说是对统治者的绝大讽刺,下面的一答不仅倾吐出百姓的怨苦,而且也揭出了官府卖盐的敛钱实质。
黄庭坚此行本为销盐征赋而来,但百姓的惨状却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同情,对榷盐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这就和他本身的使命职责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在诗中将这些矛盾揭示得也很深刻,试看《丙辰仍宿清泉寺》:
山农居负山,呼集来苦迟。既来授政役,谣诼谓余欺。按省其家赀,可忍鞭抶之!恩言谕公家,疑阻久乃随。滕口终自愧,吾敢乏王师!官宁惮淹留?职在拊茕嫠。所将部曲多,溷汝父老为。(《外集注》卷十)
这一席内心独白将他矛盾重重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作为官员,他要为国家利益尽职,同时又有抚循百姓之责(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处于这两极之中他感到无所适从。这种矛盾心态在长诗《己未过太湖憎寺,得宗汝为书,寄山蓣白酒,长韵寄答》中刻画得更为深细:
尚馀租庸调,岁岁稽法程。按图索家资,四壁达牖窗。掩目鞭扑之,桁杨相推枨。身欲免官去,驽马恋豆糠。所以积廪盐,未使户得烹。八月酾社酒,公私乐年登。遣徒与会稽,而悉走荻篁。吾惟不足遣,夙驾略我疆。...夙夜于远郊,草露沾帷裳。入磴履虎尾,扪萝触虿芒.....税驾乱石间,岩寺鸣疏钟。山农颇来服,见其父孙翁。苦辞王赋迟,户户无积藏。民病我亦病,呻吟达五更。韵为诵书语,行歌类楚狂。(《外集注》卷十一)
此诗可以说是当时杜会生活的一个实录,其现实主义的真实与深刻力追老杜,毫不逊色,它反映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一个怀有仁政理想的官员在这种矛盾中无以自处的尷尬困境。
这些诗作表现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它们体现出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甚为感人。就在庭坚写这些诗的同时,即元丰五年三月,提举江西南路常平等事刘谊上书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不久又再度上书,详论新法推行中的种种弊端,指出“造法之臣不愿陛下惠民本意,一切以利为,......大抵妄意朝廷志在财用,希合而已”。之后又上书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置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于今民间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月钱欠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盜贼,其将奈何!”(李焘《续資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四,以下简称《长编》)庭坚的诗作与刘谊的奏疏可谓异曲同工,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同样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严重社会问题,表现了同样的对统治前途的忧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作于苏轼的“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狱,于元丰三年谪居黄州,庭坚却并不因此而有所畏缩,写下了十多首揭发时弊的诗作,确实表现了他的良心和胆识,当时刘谊即因上书言事而遭勒停,可见提出政策上的异议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黄庭坚的仁政爱民思想不仅集中表现在这些反映榷盐扰民的诗作中,在其他诗中也时有流露。如《寄李次翁》诗中称赞李次翁:“颇似元鲁山(唐元德秀尝为鲁山令),用心抚疲弱,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外集注》卷十)其实这也是庭坚的夫子自道。又如《答永新宗令寄石耳》一诗乃为答谢永新(太和邻县)县令寄赠石耳而作,石耳是一种地衣类植物,生于深山岩石上,可采作珍稀食品,诗的后半写道:
吾闻石耳之生常在苍崖之绝壁,苔衣石腴风日炙。扪萝挽葛采万仞,仄足委骨豺虎宅。佩刀买犊剑买牛,作民父母今得职。闵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鲑莱烦嘉禾(永新县别称)!愿公不复甘此鼎,免使射利登嵯峨。(《外集注》卷十三)
诗人感慨石耳生长于高崖绝壁之间,受风吹日晒,采集非常不易,要攀缘高山陡璧,一不小心还会葬身虎口。他想到了汉代的龚遂,劝民务农,使持刀剑之民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又想到了东汉的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安邑令经常派人给他送猪肝,他知道后叹日:“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终于离开了安邑。诗人追慕前贤,不愿以口腹之欲给百姓增加麻烦,也委婉地规劝宗令,不要因为偏爱这种食品而驱使人们为谋利去冒险。诗人让一首普通的答谢诗闪耀出积极的思想意义,正是因为他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在太和期间他曾摘取蜀王孟昶《戒石铭》中的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书以勒石自瞥。凡此种种都说明他的思想品格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尽管庭坚在太和任上不甚得意,内心颇为矛盾苦闷,但在和旧雨新知的交往中还是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在和他们的唱酬中,他可以袒露自己的心扉,一吐胸中的抑郁块垒。如元丰四年作《次韵和答孔毅甫》及《再用旧韵寄孔毅甫》两首七言歌行,写得磊落顿挫,充溢着慷慨不平之气。孔毅父(甫)名平仲,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与兄文仲(经父)、武仲(常父)俱以文名,合称“清江三孔”。诗中倾吐出基于共同遭遇和秉性的相知相惜之情,他们都沉沦下僚,穷愁寂寞,因而发为怀才不遇之叹。诗人称孔毅甫“气与神兵上斗牛,诗如昭雪濯江汉",而自己则“窃食仰愧冥冥鸿,少年所期如梦中”,平生的知交或逝或散,在此落寞生涯中唯有毅甫视之为知己,所谓“自说中郎识元叹",即以蔡邕之赏识顾雍比毅甫对自己的知遇。第二首诗的最后写道:“太阿耿耿截归鸿,夜思龙泉号匣中。斗柄垂天霜雨空,独雁叫群云万重。何时握手香炉峰,下看寒泉濯卧龙?”(《外集注》卷十)“太阿”两句虽然意谓得到了对方的书信,勾起了相思之情,但那长剑倚天、夜鸣匣中的意象却让人感受到不甘陆沉无为,渴望奋发蹈厉的浩然心态诗人在寂寞中对友情的渴求表现出他十足是一位性情中人。此外,他与周寿(字元翁,周敦颐长子,时任吉州司法参军)、余卞(字洪范,赣州郡掾)、陈吉老(太和县丞)等的交往唱和都反映出这种志趣相投、肝胆相照的真挚情谊。
除了友情的慰藉,庭坚还在山水佛禅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吉州不仅山水佳绝,而且禅宗法席鼎盛吉安东南三十里处有青原山,六祖慧能的法嗣行思在此建静居寺弘法,开禅宗青原一系,故被称为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并重于世,成为慧能之后禅宗的两大系统。庭坚来游此地,不仅为山水所陶醉,而且也被浓郁的宗教氛围所感染,使他的灵魂得到抚慰,在出世归隐之想中化解尘世的烦恼除青原之外,他的足迹还遍及吉州及邻州的其他山水及寺院,留下了众多的题咏,发挥了超尘出世的思想。后世传诵的《登快阁》七律就是这一时期他的精神境界的最好写照: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睛。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外集注》卷十一)
高远的天地澄澈的江月使他从繁杂苦恼的政务中解脱出来,顿觉境界开阔、心胸豁然。颌联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因为它写景如绘、意境高远,更因为它映照出浩然豁达的胸襟气度、崇高酒脱的人格境界。以绝弦叹知音之稀,以美酒寄人生之慨,最后归结为乘归舟长笛、与鸥鸟为盟的超尘出世之想。
全诗勾勒了他在太和时期寻求解脱的心路历程。
元丰六年十二月,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属山东)他趁调任之隙回了一次老家,在翌年的夏秋之间到达德平此时的德州通判为赵挺之。挺之字正夫,金石学家赵明诚的父亲,也就是光耀中国词史的女词人李清照的公公。庭坚居官德州时与他有了交往,《外集》卷十一收有《寄怀赵正夫奉议》及《四盯卯对雨寄赵正夫》二诗。第一首云:“鸳鸯求好匹,笙磬和同音。何时闻笑语,清夜对横琴?”第二首日:“赵侯乘金玉,不与世同波。从容觉差晚,鄙心寄琢磨。”从诗中所写来看,庭坚是将他视为知己的,对他不乏称颂之词,且有相见恨晚之叹。但也正是在此时,他们两人之间已暴饌出政见的分歧。苏轼在元祐三年十月在上书中曾述及:“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葉,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长编)卷四百十五)这一分歧埋下 了此后不和的种子,直至后来赵挺之罗织罪名,导致庭坚贬死宜州。
关注微信号:雅墨客书法讯息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