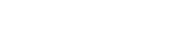草书欣赏和创作的关系(2)
构图的美感
孙过庭在《书谱》中有过一段名言:“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这段所说明的“违”与“和”,是一切艺术形式美的规律,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草书线条以及线条和线条的组合也同样要符合这一 美的规则。
线的多样式,主要是指用笔过程中运用提按、顿挫轻重,疾徐,所产生的线的浓淡、干枯、粗细、方圆、涩润畅滞等效果,在一张草书作品中一定要合理地将这些变化运用进去,这是因为“多样性为美所必具”的。例如,万岁枯藤”的雄劲苍老线条是美的,但如果从开始第一笔直到结束,都使用同一种笔法墨法贯穿到底将会使图面呆板僵死,再美的线条也不会美了,所以纵观古今草书名帖无不是将各种变化巧妙地融人作品之中,而且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体现着对比、强化的效果。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带躁方润、将浓遂枯”,就是说为使润线更有血骨感,一定要用“躁”线与之对比方显出润的本色。“浓”和“枯”是对立的,将“浓"、"“枯”的线条同时运用时,则会使浓者更浓,枯者更枯。因为任何事物总是相对的,总有一一个参 照系数,“浓”是相对“枯”而言的,同样方圆,粗细、轻重、疾徐,也合于这个原理。再说,人们的审美心理,也同样是希望多样性的,谁也不愿去看同一张亳无变化的面孔重复出现。
但是对于“违”来说,也绝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味地“违”下去,而是要在“不犯”的基础上变化的,这样才符合美的形式规律,也就是说多样要在统一的基础上的多样。对草书的要求则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我们说草书具有音乐的素质,音乐总有自己作品的基调、主旋律,草书也是如此,每一幅作品总有自己的用笔基调,无论是雄伟,或是飘逸,是流畅线,还是挣扎线,总有自己的情感基础,总是在此情感基础的波动上,产生节奏韵律,制约着线条的轻重,疾缓,浓淡,千湿。因此草书作品中,绝不能为求变而变,而应根据自然的节奏运动进行各种变化。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那将是形式的堆砌,虽然好像是变化万千,实则是杂乱无章的并无生命感和美感可言,因此,变化是在整体风格基调上的变化,是艺术多种样式统一中的变化。
草书线条的多变统一性 ,是依靠节奏气的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这种连接虽说是时间序列性的连接,但是作为展示给读者的却往往是整体的线与线的关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也即是所谓结构和章法。在“违”与“和”的调协关系中,草书的构图具有着强烈的美的信息。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山川壮丽的美景,古松的依势盘曲。的确,山川的奇妙,是无于伦比的,而古松以主干为其重心底座,上下左右自然的伸展,不平衡中的平衡,不对称中的对称,确也是造物的杰作。而草书的构成却正是来自“世间万物”。于山川乃至万物为取态的对象,“囊括万殊,裁为一相”。把山川万物优美的形态,融人抽象的构图之中。也有人喜欢将书法和舞蹈相比,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大进,更是书史上的佳话。这中间虽有时间过程中的气韵、力感等因素,但也不可否认舞蹈中那连续不断的一个个舞姿造型对他的启发。但是草书毕竟是草书,它并不代表每个具体的物象,或者某个具体的舞姿,它是运用“世间万物”构图美的一些共同的规律进行自身的美的创造。在前面所提到的古松盘曲中的不对称的对称,不平衡的平衡以及舞蹈的伸展开合,各种力度的平衡,各组动作的组合连接。这些美的特征,都为草书所吸收所运用。怀素在和邬邦及颜真卿对话时说过自己对草书创作的体会:“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他从夏云中所见到的那种自然的变化无穷的形象,是属于“迁想妙得”的艺术通感,并不需要在草书中画出具体的夏云形状。因此,草书在结构章法中所表现的艺术通感,正是它打动观赏者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形式美之中,以对称、秩序、和谐、平衡、节奏为美,这些美感形式在草书的图形中均有表现。
从草书的字法要求来看,它总是在一个规定的序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是再复杂的字,也总有它穿插连带的过程。所以王羲之的小草虽说字形较为独立,但笔划与笔划之间、字字之间常常是笔断意连,序列性十分清晰。张旭的狂草,大起大落,狂放不羁,然而牵丝映带、主笔副笔清清楚楚。它们都是在一种序列中有井有条的进行的,绝不会是杂乱无章的。这些书家就是项穆所说的“真手”,他们在作品中总是体现着秩序的美感。反之,一些不成功的草书作品,则在序列上交待不清、给人一种含糊的印象,因此在构图,上则必然是杂乱无章的,是不符合美感要求的构图。
平衡,在一般人心目中以为是对正体而言的,而草书之宗旨在变化、在不平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草书也是十分讲究平衡的。草书的平衡是把平衡的范围扩大了,有时不是局部的或单字之内的平衡,而常常是二三字,或者一行,甚至一篇作为一个平衡的基准,王铎的这种平衡是几组的平衡,行与行之间二三行关系平衡。而徐渭的平衡,则是整体的 。它不可抽出某一个字,或某一行来谈平衡,这种平衡实则是更难掌握的平衡。
草书的平衡,有时已不是单单依靠黑字来求得平衡,它往往扩展到字体黑线之外的空白处来进行,而往往是要依靠黑白的感觉重量来分辨作品的平衡与否的。
草书的平衡是和变化结合在一起,草书受强烈的情感驱使,在动荡多变的线条和构图中,对原有的平衡作出各种各样的破坏,制造出很多不平衡的因素。然后随着节奏的进行,又在组织着新的平衡解决着这些不平衡的因素,使之在大的组合上达到了新的平衡。所以说草书的平衡是多变的,更具有艺术特色的平衡。
草书的节奏韵律,是在序列的过程中由各种轻重疾徐的变化而造成的,草书的节奏感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第一个 方面是线条的序列过程,也正是,上文所谈的书法的音乐性,这是指草书在书写的时间过程中作粗细轻重,疾徐的各种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受到情绪的制约,可能是平缓的,也可能是激昂的;可能是一个节奏贯穿始终,也可能是多层次的节奏变化。可以说由于情绪的不同,表达情绪的方式不同,时间性所带来的节奏感也就不会相同。王羲之有王羲之的节奏,张旭有张旭的节奏,怀素有怀素的节奏。
第二个方面,是既成作品的视觉效果。由于草书用笔的浓淡干湿,字形的大小,笔划的曲直,位置的安排,以及黑白的疏密,字势的动荡也是在一一个空间序列中分 布的,它会给人产生视觉效果的节奏,这是草书的空间特征所带来的,如王铎的这篇草书。我们撇开时间性线条序列所产生的节奏,单从字形外表来看,其轻重、干湿、大小定势,出现了一个个动荡的节奏,从而产生韵律感。这种动荡的韵律感是人们对平面字形的重心点和黑白分割以后的动荡感所造成的。
成功的草书作品,应当在序列中通过各种对比作和谐的符合艺术规则的变化,这样才能成为创作的“真手”。如果在时间序列中,或者在空间的序列中这种和谐运动出现明显的断点,忽重忽轻,忽大忽小,破坏了节奏的序列性,是不能给人产生节奏美感的。对于节奏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和谐 ,这一问题从音乐方面来说是较易理解的,因为音乐不和谐便是噪音了。对于草书来讲也是这样。每一张草 书作品一定是一 一个和谐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韵律基调,如果是杂乱的拼凑,就会和音响一样成为“噪音” 。将会使欣赏者避之犹恐不及了。
神采之美
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道之妙,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句话说明了书法作品的要求总是以神采为主要的。这里所说的神采,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作品的形式透露出作者的精神面貌,审美观念和学识修养。所谓王羲之的字“冲和飘逸”,是魏晋名士的代表,就是王羲之作品中的神采给人带来的感觉。
草书作品的神采,也同样是指草书中通篇的精神面貌,除了王羲之飘逸,还有像张旭的狂放雄浑,以及所谓典雅、秀媚、文人气息、金石气息等等。这些精神面目,都是作者的审美趣味和修养的体现。所谓“书如其人”或“书为心画”,实则所指也就是如此。然而神采绝非游离于作品之外的一种东西,一定要通过形质表现出来的。欣赏者也只能通过形质去体会,去品味。究竟神采是怎样通过形质表现出来的,这一点很用语言文字说清,有时只是对具体作品的感觉。从大的方面讲,草书线条的组合和章法的安排,以及节奏韵律的运用,是受作者的感情和长期养成的审美观念制约的。而气质、生活作风、时代审美趋向,又对个人的审美观念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平时缺乏个性、随波逐流之人,只会写出符合一般人赏识的平庸之作,不会有什么个性强烈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用笔、构图、结字、韵律,不是为自己而作,而是为市俗所书。而像张旭狂草的狂放不羁、超凡脱俗的雄风,是和他“脱帽露顶王公前”的气度,以及“大叫三两声”的狂放性格分不开的。因此在他的草书中,那种明快的节奏,强烈的对比,一气而下的气势,正是他人格的写照。而那些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不成功的草书作者,却十分注意每个笔划是否中锋,字体牵连的长短是否和名家一样,这样写出的草书,也必然拘谨,出现一种奴气。从以上种种事实来看,要想深刻地去品味草书作品的神采,最好是多了解一下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精神面貌,它会使人更深刻地去品味草
书作品的神采,比如徐渭作品的狂放,并不同于张旭,张旭的狂放有一种自信感,给人是一种豪迈的感觉;而徐谓的狂放,给人是一种压抑的爆发性的狂放,一种一吐心中闷气的狂放。反过来说,对两个狂客神采的不同感受,也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生活的社会及他们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上去得到印证。
另外欣赏对创作还有制约的作用。创作先于欣赏,这是一般的常识。对于书法来讲,又由于从产生起就伴随着使用文字并与之同步发展着,所以欣赏是在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汉末魏晋以来,随着书法艺术的自觉,欣赏品评书法成为时风,也正是由于这种时风,才促使中国书法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说没有欣赏群就很难有自觉创作的作为审美存在的书法作品。这是因为欣赏和创作是相互作用的。
在书法欣赏领域中,草书欣赏群是最早出现的,这一点在汉末《非草书》一文中有所记载。汉末这群欣赏者的出现,是造成各类草书最终定体的原因之一。在魏晋和唐代这两个草书的高峰期也都有欣赏群的记载,像王羲之书扇而纨扇涨价,王献之书纱械而被众人争分,张旭的狂草“令王公粉墙素屏”以待书写。这些记载虽说是讲创作的力量,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欣赏者也刺激着创作者的艺术方向。
在书法的发展历史中,常有某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影响后世的创作,像王羲之影响唐代书风就是一例。这种影响后世创作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后世对前代书作的欣赏所造成的。
对于草书来说,因为它不担负过多的实用文字所需要的社会功用,常是以欣赏的面目出现,所以在学习草书过程中,总是以欣赏为先导的。当书写者在欣赏过程中对此种书体出现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学习和创作才会起步。同时,创作过程中又常常通过欣赏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草书创作来启迪自己的审美观,校正自己的创作方向。所谓某某人的草书,出自前朝某某人,也正是欣赏、学习所造成的。
当然正像创作一样,欣赏群也是复杂的,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也就会出现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有些好的作品往往不一定被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绝不能认为这些作品没有欣赏者。有时则是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格调较高,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罢了,但它却会得到虽然人数不多,却是见地极高的欣赏者嘉许。比如徐渭,他那种狂放的雄风,并不被明末董其昌的崇拜者们所欣赏,反而常常被这些人称为“野狐禅”,但同时代的“公安诗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却评论他的书作是“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说明在当时还是有很多独具“真眼”的欣赏者作为他创作的土壤。
由此可见,欣赏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作用而一起发展的。创作引导欣赏,欣赏又反过来校正创作。这两者交错着把中国的草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
关注微信号:雅墨客书法讯息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