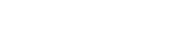汉碑文学特征
东汉中叶以后,文学观念的演进,文人审美意识的增强,使得文学创作在形式风格上呈现出时代的新特征。碑文作为一种有着特定写作对象的应用文体,有着其特定的语言形式和规范。但是作为东汉文学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同时受到时代审美观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汉碑的语言形式和艺术手法的总体特征是与同期的文学变化一致的。
典雅庄重的语言特色
隶事用典
信古、崇古是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对过去时代的追慕,对往古的迷恋,沉淀于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在两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们浓烈的崇古心理,又外化为尊经的社会习惯,直接表现为对古代典籍的崇信,当时“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依据",因此彪炳六经,稠叠纬侯,构成了两汉文化对经典的特殊依赖。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当时的创作,各种文体都深受经学的浸染。因此东汉之文,多引经据典、融化经书以为己用,碑文亦是如此。
“汉碑雅训,词句皆有所本,不可目以剽窃。经子成语,触目皆是。”汉碑引典,主要出于儒家经典,以《论语》最多,其次为《诗经》、《尚书》、《周易》、《左传》《孟子》、《礼记》,《谷梁传》、《公羊传》最少2;另外还波及史书如《战国策》、《史记》,先秦子书如《管子》、《晏子春秋》《文子》、《韩非子》《墨子》《鬼谷子》等。在行文时或化用经书文句以助文笔,或引用经史典故以形容表象,形成语言典奥、风格凝重的特色。汉碑创作,用典多采用儒家思想,且为文多推崇圣人的思想,一方面与碑文述亡颂德的文体特征有关;另-方面,也体现了东汉的时代文风。
汉碑中引典,主要用典来形容,以典故比附事实,因此往往可以不分地位,使用随意。赞圣人之语,不妨施之童稚,如“克岐克嶷"原称后稷聪明,而《童子逢盛碑》亦可用来形容儿童:“早克岐嶷,聪明敏达。”《泰山都尉孔宙碑》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罪己。”国孔宙为人臣,而引禹、汤作比。欧阳修评之为“盖汉世近古,简质犹如此”。而六朝以后,形容词用法甚严,状拟君王之词绝不能施诸臣民;同时用典的范围更为普遍,由经书旁及子、史、集、百家杂说佛道之语。
汉碑中一部分资料,以见隶事用典之大概情况。汉碑之用典,有语典、有事典。因为汉碑多以四言句式为主,因此在引经据典时,就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将原典熔铸为新的词语,用在句中,使典故的运用符合碑文四字格的要求。在具体构成方式上有很多种,其中以缩略式和割裂式构成为最主要。
缩略式是在不影响表达的情况下,简缩典籍语言的片段,形成缩略式语言固定搭配,使其具有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的凝固性。如生荣死哀,《敦煌长史武斑碑》云:“生荣死哀,是口万年。”语出《论语●子张》:“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高山景行,《淳于长夏承碑》云:“高山景行,慕前贤列。”语出《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彬文赳武,扶弱抑强。”国彬文、赳武,语出《论语●雍也》“文质彬彬”与《诗经●兔置》“赳赳武夫”。缩略为“彬文赳武”,用以赞颂潘乾文武兼备。
而割裂式则是随意割裂所引典籍文句的一部分,构成特定含义的四言句式。如“有朋自远”。《玄儒先生娄寿碑》:“下学上达,有朋自远。”从《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割裂而成。《博陵太守孔彪碑》:“仁必有勇,可以托六。”国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中割裂而来。《司隶从事郭究碑》:“昭德塞违,克纪克纲。”语出《左传●桓公二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姓。'”,通过对语源材料的加工,使之变为整齐匀称的四言句式。无论是哪种方式的使用,都可以使汉碑语言意蕴深厚,典雅凝重,用最简洁的形式,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极具表现力。
这些意蕴深厚的四言句式在使用中逐渐固定下来,因此产生了很多成语,大部分流传到现代汉语中一部分 成语则成为后世成语的发展的源头。据有人统计,东汉明确源流的碑刻成语以出自经部书籍的最多,其中出自《论语》30条,《诗经》14条,《尚书》、《周易》各8条,《左传》6条,《孟子》3条,《礼记》2条,《谷梁传》、《公羊传》各1条;其次出自史书共6条,《战国策》5条,《史记》1条;源于子书的成语:《管子》2条.《晏子春秋》、《文子》、《韩非子》、《墨子》、《鬼谷子》各1条。这个大概的统计数字,已经能够充分体现出汉碑语言隶事用典的特色,也反映了汉代碑刻语言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东汉碑文中用典情形的普遍,用典技巧的日趋成熟,显示出碑文用典已经成为东汉文人创作的一种文学自觉。
二、锤炼词句,讲究文采,语尚骈偶
东汉文风整体.上有骈化的趋势。“从文章体制上看,东汉中期以后,骈俪之体已渐渐脱胎,成为文坛上的主潮,影响及于各种文学体裁,开始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因受这种时代文风的浸:染,碑文的创作也毫无例外地受其影响,具有骈文的一些特点,语言华美,富于文采。
汉碑语言的演变趋势是逐渐由散体向骈俪发展,早期汉碑仅简单叙事,语言平实乏采。而东汉中期以后的汉碑开始有意追求语言形式的整齐、骈偶,显示出逐步成熟的对偶技巧,而且文辞上有日益明显的藻饰趋向。这个趋势与东汉文学的复苏步伐是一致的,是作家审美意识与文学观念觉醒的标志,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进步。
早期汉碑多以四字句为主,对偶句式一般为四字句对四字句的偶对形式,在碑文叙事中出现。如《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残伪易心,轻黠諭竞,鸱枭不鸣,分子还养。”后来出现了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甚至八字句的对偶句式,如《河间相张平子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堂邑令费凤碑》:“修孝友于闺阀,执忠蹇于王室。”《孔谦碣》:“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圆有时同字数的对偶句式在碑文中往往成组出现。如《郎中郑固碑》:“孝友著乎闺门,至行立乎乡党。初受业于欧阳,遂穷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学,襄冉季之政事。”《泰山都尉孔宙碑》:“田睃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险路。会鹿鸣于乐崩,复长幼于酬酢。”有时则句式长短错落,或以四六句式对偶,如《冀州刺史王纯碑》:“穷则乐善,达则口人。进则延宾分禄,退则却扫闭门。”或以分句形式,前后隔句对偶,句子字数长短随意。如《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君幼有岐嶷天然之姿,长有明肃弘雅之操。刚毅多略,有山甫之纵。沉懿敦笃,为万夫之望。”《沛相杨统碑》:“德以化圻民,威以怀殊俗,慕义者不肃而成,帅服者变衽而属,疆易不争,障塞无事。”这种长短错置的对偶句式,对仗工整,而又变动不拘,使庄重典雅的碑文平添华美流畅之韵味,极大拓展了碑文的文学表现能力。
而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四十余篇蔡邕撰写的碑文中,虽然其文不尽是骈俪,但传世佳篇,皆以骈俪著称。如《郭泰碑》叙郭泰资禀学行日:“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采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收文武之将坠,拯危言之未绝,于时缨缕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陈宴碑》一叙陈蹇的德行政绩云:“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兼资九德,总修百行。于乡党,则恂恂焉,彬彬焉,善诱善导,仁而爱人,使夫少长,咸安怀之。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徼讦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谧。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淡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这些碑文中已经有很多标准骈句,文采富丽,音节和雅,即使置之骈文成熟的齐梁时代作品中亦毫不逊色。蔡邕的后期作品已经高度骈俪化,对偶句式更加密集,锤炼更加精工,而且句式长短相间,多排比使用,既使音节整齐匀称,韵律感强,又使语言气势增强,感情得到加深,气脉贯通,酣畅淋漓,展示出在对偶技巧运用方面的娴熟流畅和精审自如。因而蔡邕被认为是“汉末大骈文家”国,其《郭泰碑》也往往被认为是骈文的最初作品,收入各种骈文选中。而在同期的汉碑中,虽然由于作家自身才华素养不同,其作品中骈辞俪句不如蔡邕碑文的密集和锤炼精工,但也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东汉碑文创作中对偶技巧日益熟练的发展轨迹。
汉碑中对偶句式,有长有短,一般多为四句,六句亦常见,七句较为少见。《文心雕龙●丽辞》云:“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国观东汉碑文,言对为多,事对为少,正对为多,反对为少。正对多,反对少的现象,部分因为碑文是一种叙颂死者生平德业的文体,在创作时一般多选取盛赞死者的丰功伟绩,同言对多、事对少一样,也因为对偶技巧在东汉时尚不十分发达的缘故。虽然东汉碑文的对偶在技巧方面不若后代对偶方法多样,技艺精湛,转承自如,毫无滞涩,但是已经具备了作为对偶的基本形式,掌握了基本技巧。这些对偶句从形式上看,节奏鲜明,音调铿锵,朗朗上口;从内容上看,凝练集中,概括力强,因此在汉碑中广为运用。由此呈现出汉碑骈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注微信号:雅墨客书法讯息应有尽有